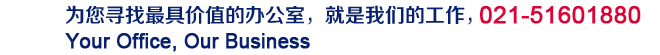2017年初召开的上海“两会”宣布,今年全市将在去年“拆违”6000万平方米的基础上,再拆除5000万平方米的违建。而北京最新公布的官方数据也显示,今年前5个月,该市拆除“违建”超过2000万平方米,这是其全年“任务量”的一半。
近年来,对于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来说,城市管理和规划的首要命题似乎就是清理城市低端服务业和看上去“脏乱差”的市场。这样的清理行为,在许多城市规划者甚至于很多市民看来,似乎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题中之意。于是乎,大面积的小商铺、小市场逐渐从街边消失,一座座高档的写字楼、购物中心在官方的规划图上跃然而出,一片片绿地和公园也在高档社区间星罗棋布。
诚然,城市的升级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事情,但借助“行政手段”大面积地强制性拆违,是否合理,依旧值得思量。放在更大层面来考虑,这样的城市升级背后,事实上还指向更大的问题:中国这样的“大国”发展到今天,需要怎样的“大城市”?是外表鲜亮,却门槛极高而缺乏包容性的城市,还是那些面貌光怪陆离却敞开胸怀的城市?
但无论是城市发展,还是产业升级,让我们来判断个中决策正确与否的,我想仍然应是它们是否符合一般的经济学常识。
正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这所说,依靠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国际上的普遍案例,来重新审视我们当今的“城市发展之道”,才会避免在讨论城市化战略时“纸上谈兵”,也才会避免我们在讨论时陷入“利益之争”。也因此,陆铭的《大国大城》就显得难能可贵: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今天我们城市化进程中的病灶,让我们反思这个过程中内心的那些“自私”和“短视”,更催促我们重新寻找到正确的城市化道路。
城市化的意义,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恐怕是毋庸置疑了。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促使规模经济的生发。正如陆铭在《大国大城》的第一章里就写道的,“大国的规模经济对中国来说越来越重要”,这样的规模经济一是可以帮助我们发展诸如大飞机等大型、高端的“战略性产业”,二是帮助我们实现技术创新——只有产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才能为技术创新提供土壤;第三,则是可以更好地提供公共品服务,例如导航系统、医疗服务等,只有城市达到一定规模,这样的公共品才能拥有足够的市场需求;第四,则是助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教育、文化、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发达,无一不需要依靠规模化的城市经济。
也正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命题,就是尽可能地孕育和壮大规模经济,增加都市经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样才能有效地推动宏观转型的成功。正如城市规划学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到,“健康的大城市的功能是混合的,多样性很重要。如果过于单一,社区必然会走向衰败”。
遗憾的是,对于规模经济认识的不足,事实上也造成了中国的城市政策一直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殊不知,这种控制其实就是在限制中国超级大都市的产业裂变速度,同时也遏制了促成技术创新的个性化需求的产生。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年来在大城市里出现的“网红”经济,一方面是网络时代出现的特别现象,但更重要的是城市人口多样化到一定程度后,个性化经济繁荣的后果。只有市民群体的多样性足够了,各种个性化需求才能形成足够的市场,以吸引商业资本和技术来生产和研发相关的产品,这样才能使城市经济真正形成良性的升级和发展。
更重要的是,陆铭还提醒我们注意,城市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除去经济上的效益外,还有助于实现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一点似乎与我们惯常的认识有所不同。一直以来,我们大多以为,经济过于集中在某些中心城市,会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均衡。但陆铭却指出,城市的规模经济效益,恰恰有助于平衡区域发展不均衡,进而实现全社会的公共利益。
不过,陆铭也指出,规模经济对于公共利益的促进,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自由迁徙。为此,陆铭强调,自由移民是城市化最重要的途径,“劳动力自由流动,最终实现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均等,是大国发展唯一可行的战略选择”。从这个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城市化、规模经济、公共利益这三大目标,正是借助“自由移民”而被串联起来了。
事实上,我们只要认真的考虑一下,就能理解陆铭的这个观点,而化解一直以来的误区。东北地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近年来,东北地区的人口出现了持续流出的现象,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是,东北经济一直都是建立在以资源为基础的大型重工业之上,当资源产出已经无法承载当地的人口规模时,人口自然就会向更高收入的地区迁移。所以,东北的人口流出其实是区域经济间的再平衡,是很正常的经济现象。这样的人口流出,其实有助于当地的经济恢复,提升当地的人均产值和收入。
也因此,面对近年来大众讨论甚多的城乡差距问题,陆铭指出,“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一方面,农民进城务工和定居,收入可以成倍上升,另一方面,留在家乡的农民也可以继续依靠当地资源生活,但由于人口下降,当地的农民人均收入也获得了大幅的提高。
首先,依靠行政手段限制外来人口带来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无形中提前提高了城市服务业的成本。陆铭指出,对低技能劳动者数量的限制,结果就是相关服务价格的上涨。比如,现在城市里出现的“天价”月嫂等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还有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我所居住的小区附近被“拆违”后,一些小商铺和餐饮店消失了,早餐的成本很快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城市劳动力的价格随着产业发展出现上涨,本来是正常现象,但在行政手段的“推动”下,服务业价格出现非常规上涨,却会极大地伤害城市的吸引力。届时,低端的服务业确实被“淘汰”了,但缺乏了与居民收入水平相符合的服务业,高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就会感到生活成本快速上升而过早地逃离大城市,城市经济的规模效应自然就大打折扣了。
其次,更深远的影响是,在行政力量下,低技术水平的劳动力被挡在城市之外,不仅非自然地提高了劳动力成本,而且会非常规地使得“产业升级”提前出现。例如,当下由于缺乏足够的劳动力,许多沿海地区推出了“机器换人”的政策。在陆铭看来,这样的“产业升级”并不是由产业技术的进步带来的,而是在人口流动限制的情况下,资本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更便宜而出现的结果。这样的产业升级不是正常的经济现象,而是资本、劳动力等市场要素价格扭曲后出现的特殊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生产的依旧是传统的商品,企业的利润率并没有实质性提高,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却提前失去了向城市转移的渠道。这样的经济现象,不仅是对城市化的“扭曲”,更是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扭曲”。
那么,不限制人口流入,城市的“城市病”会不会越来越严重呢?而人们对于“城市病”的担忧又是不是有道理呢?
其中,首要争论的一个问题是,外来人口是否会对本地居民的就业和福利带来影响?对此,陆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大城市会产生“包容性的就业创造”。就是说,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而这种效应对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尤其大。但我们看到,今天大城市的人口限制政策,恰恰指向的就是低水平的劳动力。所以,大城市的就业紧张,很大程度上不是人口流入的后果,而是限制人口流入的后果。
其次,对于许多人都担忧的污染、交通等“城市病”问题,在陆铭看来,也不是由移民带来的,而更多是城市规划不当造成的。最典型的就是交通拥堵问题。在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感觉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不仅城市道路很拥堵,地铁等公共交通也很拥挤。人们下意识地认为,改善大城市的交通,首要的就是控制人口、控制汽车。但陆铭却指出,上海、北京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改善交通的根本途径。例如,在地铁交通上,上海、北京的密度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其他主要的大都市,如果有一天国内特大型城市中心城区可以实现任一地点500米范围内就有地铁站,地铁出行比例到80%以上,那么地面交通也不会出现拥堵。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城市病”背后,实质上的原因都在于城市管理者没有做出足够前瞻性的规划。正如陆铭所指出的,解决“城市病”的方子并非在于限制人口,而应该从技术和规划着手。就像简·雅各布斯所说,“当我们面对城市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生命,一种最为复杂、最为旺盛的生命……庞大的财富,巨大的生产能力,支持和使用这些东西的人才的有序的聚集”。
或许,就是这种生命力,使得很多年轻人在今天依旧保持着对北、上、广、深的向往。但当政策制定者们有一天用他们的“蓝图”抹去了这种生命力,我想那样的北、上、广、深或许表面上都成为了艾比尼泽·霍华德笔下的“花园城市”,但它们的内在毫无疑问将是空洞而苍白的,到时候等待它们的无疑将只有衰败。(来源:经济观察网)
021-5160 1880
友情链接: 上海商务中心 上海服务式办公室 商务中心出租 服务式办公室出租 浦东商务中心 黄浦商务中心 卢湾商务中心 静安商务中心 长宁商务中心 徐汇商务中心 陆家嘴商务中心 南京西路商务中心 淮海中路商务中心 人民广场商务中心 虹桥商务中心 徐家汇商务中心 中山公园商务中心 北京服务式办公室 广州服务式办公室 深圳服务式办公室 杭州服务式办公室 南京服务式办公室 北京商务中心 广州商务中心 深圳商务中心 杭州商务中心 南京商务中心 写字楼出租 创意园区